
从行政前置行为探究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困境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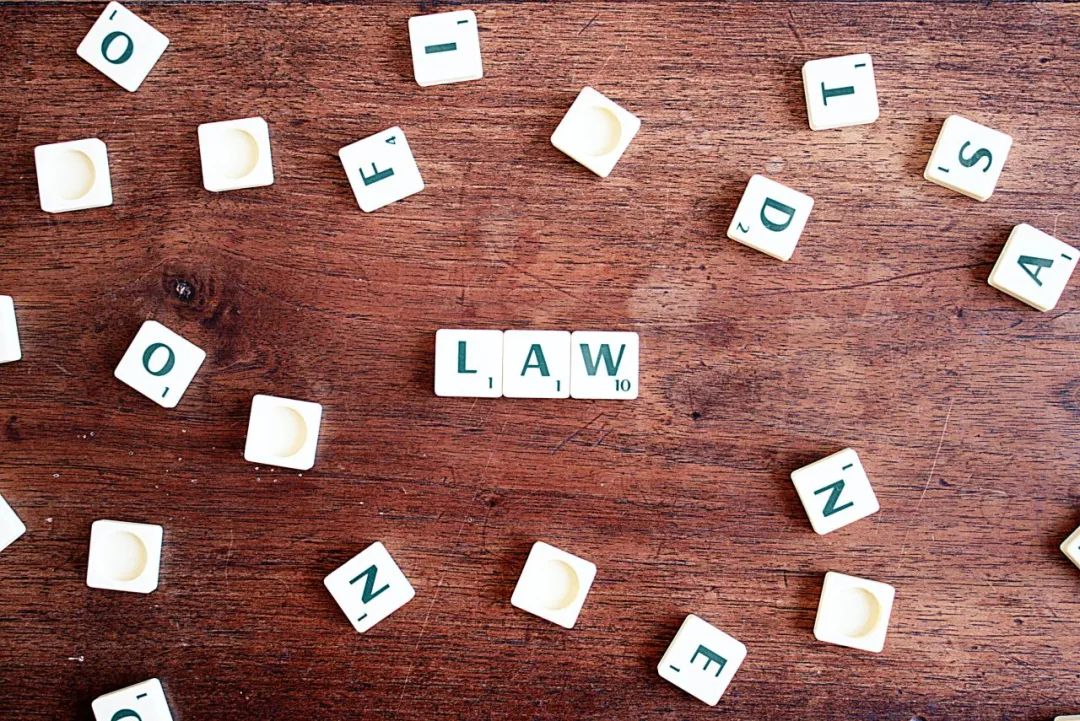
一、背景概述
刑法将危害社会公共法益的犯罪行为入罪,来维护社会和谐。因此任何罪名被规定在刑法中都有其原因。自互联网时代来临后,人类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批网络犯罪开始涌现,有以网络犯罪形式出现的传统犯罪,也有新兴的只能依托互联网才能完成的犯罪。
有学者将这两者进行分类,前者是不纯正网络犯罪,后者则为纯正的网络犯罪。本文将展开的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就属于后者,刑法设置此罪的目的有三,第一是为了促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协助管理、维护信息网络空间安全,第二是通过将网络服务者的安全管理义务纳入法条,以此来强制其履行义务,强化责任意识,第三增设该罪能够使网络空间有序运转。
但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自颁布以来,在司法文书的判例网上能查到的案例不超过十例,从侧面反应了此罪的适用率低,恐有沦为“僵尸罪名”的可能。笔者之前已就该罪在适用过程中的行政前置行为的消极性存在的一些困境展开了描述,本文将就这些困境的对策进行探索。
二、规范该罪行政前置行为的性质和定位
根据《刑法》286条规定【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根据此条规定可知,该罪的适用可以被划分为两步走。第一步:网络服务者不履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后,经相关的行政机关督促监管后而拒不改正。第二步:在前者的条件设定下再开始适用《刑法》中的相关规定。由此可知,两步走中的第一步是第二步的前置行为,也就是本文围绕的主题“行政前置行为”。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中的行政前置行为是指网络服务者经过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后而拒不改正。
由此可能会导致该罪在适用时的,刑事违法性依附于行政违法,而模糊了犯罪构成的独立性。理由是行政犯和刑法犯保护的法益不相同,二者之间的联系不应为必然性联系即违反行政前置行为不必然意味着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产生,具备该罪的刑事违法性也不必然意味具备行政违法性。
本罪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使网络服务者履行义务,而后拒不履行行政命令的才会具备刑事违法性,而类似的行政不法行为是指违反行政法规定的网络服务者的安全管理义务。因此,在适用该罪时应当保持该罪的独立性即本罪的认定与行政前置行为的程序设定应当相互独立。
三、明确“责令改正”的行政主体
根据刑法规定该行政前置行为是由监管部门作出,但是并未明确具体由哪个行政机关作出。学术界希望立法机关能够明确的规定该监管部分,但是立法机关并没有采纳该建议,作出的仍然是概括性规定。
《办理信息网络案件解释》规定,监管部门包括网信、电信、公安等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承担信息网络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其中,网信部门是指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及其下设机构,电信部门是指国务院工业和信息部及其下设机构。除了网信、电信和公安部门外,国家安全部门、国家保密部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等部门,均具有网络监管职权,可以成为责令改正的适格主体。
因此,推行行政部门权力清单制度,对于本罪适用具有重大意义,可以明晰职权边界、便捷履职程序,有效地避免信息网络安全出现监管交叉或监管真空的情形。由于网络监管涉及的领域广泛,立法机关很难对监管主体进行详尽地列举规定,应在个案中由法官对其主体适格性进行审查,核实具有监管权限的法律法规依据,确保该“责令改正”行为的合法性。
四、增加“责令改正”的触发行为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中的前置行为是行政机关的“责令改正”,但是对于该“责令改正”的触发行为也没有明确的规定,不可将所有的触发行为都寄希望于行政机关的主动监督。还应当将网络服务者平台用户的外部监督行为也纳入“责令改正”行为的触发行为之一。
例如可以在所有的网络服务者平台中都设置一个可以直接与相关行政机关连接的功能,由该平台用户自行选择启动该功能,启动后可以就网络服务者没有尽到相应的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进行投诉。相关行政机关在接到用户的投诉后在规定期限内进行回复,如果该网络服务平台确实存在行政不法行为后开始主动介入具体事件,必要时按照法律规定作出“责令改正”的行政命令。
五、对该罪行政前置行为的规范适用
(一)行政命令应当由书面形式作出
前文说到,该罪的行政前置行为不应当成为拒不履行信息络安全管理义务的必然程序要求,行政不法行为和刑事违法性应当各自独立。同时刑事违法性的构成要件是网络服务者拒不履行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行政命令。
但是对于如何“规范适用”这个行政命令却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因此规范适用这个行政命令也是解决该行政前置行为消极性的重要举措之一。第一,行政机关应当以书面形式做出行政命令,在紧急情况下可以采取口头或者其他形式作出。理由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行为的刑事违法性是由网络服务者不履行“责令改正”的行政命令产生的,对于本罪的认定来说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作用。
不法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就要证明其确实存在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此时应当减少因行政手段偏差导致处罚范围不当扩大的影响,以规范的行政命令尽可能降低容错率,如果行政命令不规范、不明确甚至违反程序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该行政命令是否真实以及其所承载的行为是否严重,并且为了日后在诉讼过程中,最大程度的保留证据,该行政命令更应当由书面形式作出。
(二)行政命令的内容应当具体而全面
目前没有专门明确规定网络服务者义务来源的正当性和边界的法律,实践中关于网络服务者义务的法律规定又大多数存在于各类行政法规,而它们之间又存在着重合和交叉的现象。
正是如此,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命令的时候才要更加明确的标注网络服务者的义务来源及其违反的具体法律法规,增加其行政行为的公信力以及来督促网络服务者积极履行义务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次对于行政命令的“责令”的内容应当尽可能的明确,不仅包括前文提到的网络服务者的义务来源及其违反的具体法律法规还应当包括其行为的可能会造成的后果、履行的期限、不履行行政命令的后果可能性、改正期限,以及救济途经。
其中对于已经具备行政不法行为的网络服务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明确改正措施的具体方法,为了避免网络服务者对其行政不法行为存在认知问题而不知如何改正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六、结语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司法案例稀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实践中的发案量少,相反,在司法实践中,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法定的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现象并不少见,有相当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钱行刑的衔接不当,因此明晰该罪行政前置行为的必要性就提升了。
立法者在设立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前置行为之初,就希望该罪的行政前置行为可以更好的调动行刑联动,通过行政机关前置的“责令改正”行为使得众多存在行政不法行为的网络服务者改正机会,促使其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以此来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随着对该罪的深入研究也发现了,在实践中该行政前置行为设立之初的美好愿景遇到了阻碍,例如该罪行政主体的不明确、行政命令的形式模糊、行政命令触发行为的片面性等等。
由此笔者在结合实践中该罪行政前置行为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阻碍,提出了四个解决方案,分别是:行政前置行为的性质和定位、明确“责令改正”的行政主体、增加“责令改正”的触发行为和对该行政前置行为的规范适用。尤为重要的是通过明确行政前置行为的性质。
杨未希
安徽润天律师事务所
实习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