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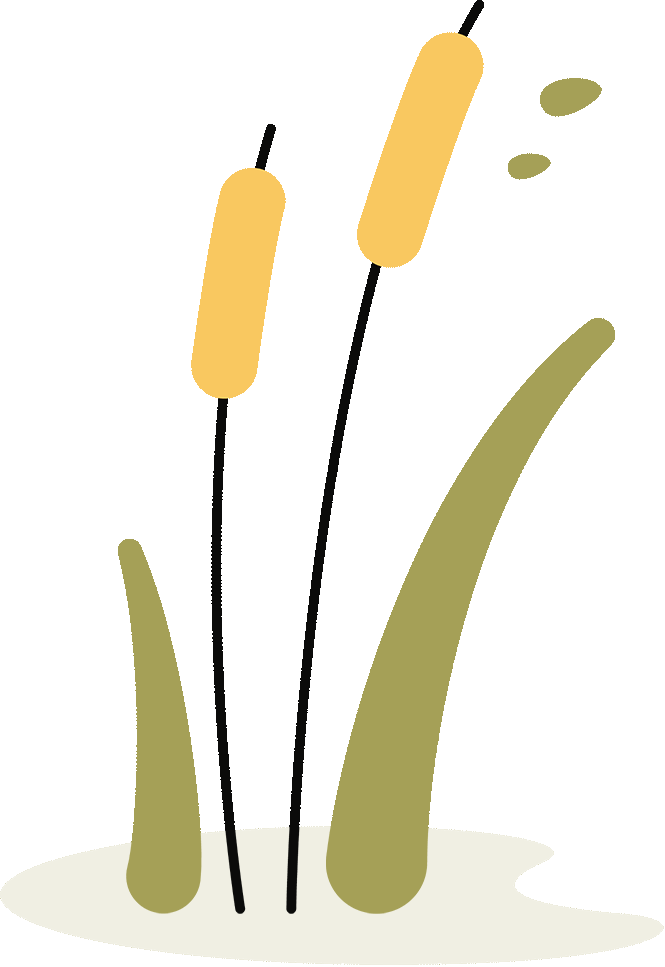
成立过失应当具有预见可能性,行为人无法预见结果的,也就不能安排自己的结果避免措施,刑法上也不能赋予行为人结果避免义务,对于结果,也就不能追究行为人的过失责任。在认定过失时,行为人应当预见到什么内容、预见到什么程度、怎样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预见可能性都是问题。
一
预见的内容及程度
对于行为人应当预见到什么样的内容,在旧过失论、新过失论和超新过失论下,有不同的见解,如按旧过失论和新过失论,都要求对引进结果的预见,而超新过失论则只要对大概会发生有一定的恐惧就足以肯定行为人的预见可能性。当然超新过失论的这种扩张的预见内容不符合责任主义,按照旧过失论和新过失论的观点,预见是对危害结果的预见,更具体地说,是对行为可能会引起什么样的结果的预见。
理论上对过失有如下两种类型,有意识的过失和无意识的过失,前者是指行为人都没有具体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具备导致危害结果的危险,后者是指行为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风险,但认为自己能够避免结果的发生。也就是常说的过于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两者的不同既可以说是对结果预见的不同,也可以说是对行为性质认识的不同。在理论上也认为,对于过失的认定,是否有意识不影响过失的成立与否,影响的只能是量刑。无意识的过失也能以过失论的意义在于,行为人不能以没有认识行为的危险性为自己的责任进行开脱,刑法上确立这种类型的过失犯,也就将能够注意到行为的危险作为一种义务赋予每一个潜在危险行为的行为人,也即,当个人安排自己行为的时候,不仅应当基于风险预见结果,也要根据自己的行为内容认识到相应的风险,那么对行为的实际认识,只要行为人能够认识到自己在实施什么行为就已经具备成立过失的行为认识的前提。
如在公共道路上驾驶汽车,只要其能认识到自己是在公共交通领域驾驶机动车,即使其是因为偶然的不注意忽视了路口的信号灯导致事故,对闯红灯的行为危险性缺乏相对应的具体认识,但留意信号灯本就是其驾驶机动车的注意义务内容,导致结果发生的是其闯红灯的行为,而闯红灯的行为是其未加注意的过失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是因为行为人的过失导致自己实施了具有危险的行为,并且这种行为的危险也确实现实化了,以此对行为人进行过失上的追责。
相反的,如果某种行为通常并不具备一定的风险,行为人在实施这种行为的时候,也就不需要具备相关的风险认识,最终的结果即使是该具体行为因为某些情况导致了其潜在危险的现实化,也不能将结果归责于行为人,除非行为人现实地认识到了这种风险而成立有意识的过失。如通常认为在地下车库的过道上,不会有人躺在那睡觉,行为人驾驶机动车出库时未加注意而碾压的,对于这种情况,不应当认定行为人有排除“会在地下停车库有人被自己的驾驶行为所碾压的”风险认识义务。对于风险认识的限定,也体现在合理信赖原则之中。
二
合理信赖与被允许的危险
合理信赖原则、被允许的危险与新过失犯理论的诞生存在紧密的联系,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工具的出现和工业生产的繁荣,社会运行的需要和风险控制的矛盾侧生了合理信赖、被允许的危险和新过失论的出现。
某些行为具有抽象的危险,但从行为的必要性和危险发生的概然性综合考量,这种危险行为只要都按照统一的准则实行,危险可以被降低在社会能容忍的限度内,是为被允许的危险。合理信赖原则是指,行为人虽然实施了具备一定风险的行为,但足以信赖自己之外的他人不实施一定的行为促使风险的实现,最终风险虽仍实现,但不以过失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行为人在合理信赖的范围内所实施的行为也可以被视为被允许的危险。行为人在合理信赖之下或实施被允许的危险,其注意义务内容的门槛也被提高,在合理和允许的范围内,行为人可以不必为行为潜在的风险而战战兢兢。信赖的原理典型应用的领域也就是交通领域,典型的如驾驶机动车可以合理信赖不会有人突然横穿马路,机动车驾驶员可以合理信赖乘车人不会主动跳车等等。当然合理信赖建立在行为人自己的行为在允许的范围之内,若行为人本身的行为已经是不被允许的,其就不能将排除自己行为的风险基于信赖指望和托付他人,这样当其风险现实化的时候,其也就有责任承担这种不合理信赖所导致的结果。
三
预见可能性的判断标准
怎样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预见可能性,有客观说与主观说的争讼。客观说认为以一般人的认知能力标准来对行为人的预见可能性进行判断,如果某一行为会导致某一结果是一般人都能预见的,便认为行为人也具有预见可能性,主观说则以行为人个人的认识能力为判断标准,如果以行为人的具体认知能力不能预见的,则否认行为人的预见可能性。有折中说对主观说与客观说进行中和,该说认为对行为人认知能力的要求不能超越一般人的认知能力,因此以一般人的认知能力水平为上限,一般情况下以个人为标准,但在个人的认识的能力高于一般人的,则以一般人为参考标准。
对过失犯不同构造的解构和预见可能性不同的体系性安放,对预见可能性的参考标准的选择和选择的理由也会存在相应差别。若认为过失犯属于与故意犯不同的不法事实类型、将过失作为构成要件要素,同时又将过失作为责任要素的立场,可能会在构成要件阶段选择一般人标准,但在责任阶段采用个别人标准,而只将过失理解为主观构成要件要素的一阶层过失理论,则直接采用个别人标准。若认为过失只是责任要素的,基于责任的个人原则,只能采用个别人标准,而不适用一般的标准。在将过失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相同前提的不同理解下,对预见可能性标准的不同本质上仍是对不法行为的理解不一致,是对人的不法与行为不法的争执。认为不法是行为不法的,更具备规范的普遍性与一致性,期待所有规范接受对象都按照统一的规范支配自己的行为,对共同规则的逾越即为不法,而人的不法则关注人的主观目的、倾向和对法的反对态度等等因素,认为人对规范的接受能力、理解能力、反对动机的形成原因都是不法应当包含的内容,而如此这些要素都是因人而异的,对人的不法评价应当考虑人个体的差别化,类似于预见可能性的认知基础,知识水平确实远低于一般人的人不慎导致了不法结果,就不能根据结果的不法和逾越了一般人的行为准线将这个人定义为罪人,除非某种能力是其应当且可以具备而怠于注意的。相反的,认知水平高于一般人的精英明明发现了其行为具有一般人不能发现的隐患仍放任风险的,法律也不能放任这种特别认知下的肆意。考虑到特别认知能力的情况,一般人标准在二阶层的过失框架下,将一般人认知作为客观预见可能性的判断标准,就容易将一般人难以预见的风险直接排除,从而相对地对特别认知行为降低了标准,仅依赖于行业规范或者并不能全面解决问题。
可以说,在预见可能性的最终认定上,将行为人个人的认知能力作为判断预见可能性更符合责任的实质内容及其使命,但可以一般人的认知能力为基本参照,可以一般的标准对其提出注意的要求,但在行为人其确因职业、教育背景的不同而具备高于一般人的认知的,或者确实难以正确认识到行为的风险以至于让其认识到属于强人所难的,则根据其具体的认知能力判断其是否应当预见和可以预见。

★
杨宜 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