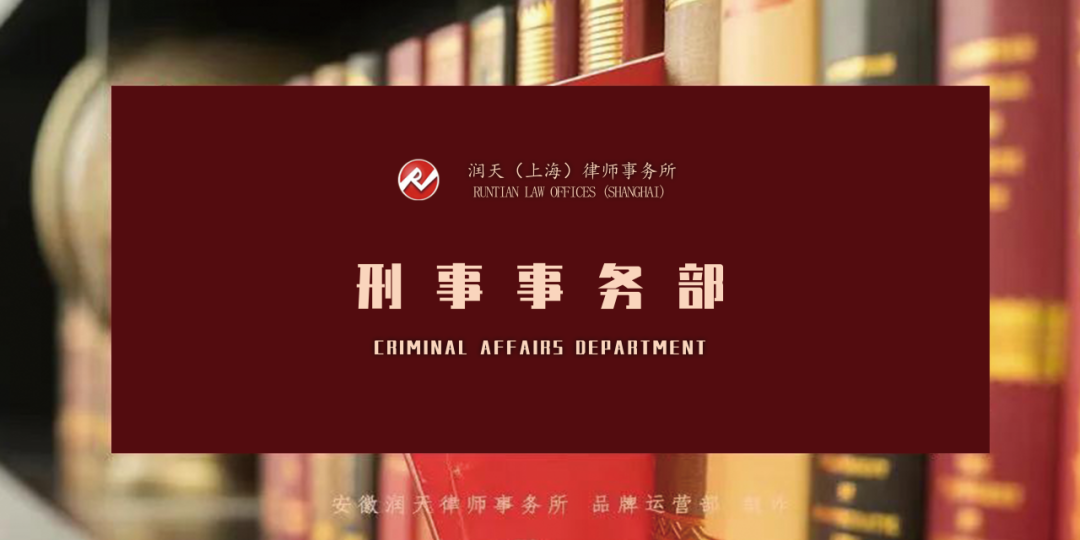
寻衅滋事罪中“”借故生非“”的认定
一、研究背景
笔者最近接待了一个借故生非类寻衅滋事案件的咨询,认为这类案件在实务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因此查阅了相关法律规定和理论文章,并做出了一定总结。
案件细节并不复杂,当事人2020年6月起即因农村宅基地办证审批事宜多次找到主管单位,但均未能得到准确答复,后遂经常前往寻找经办人,并存在多次阻止其正常下班的行为。中途主管单位的经办人亦曾报警处理,但公安出警后也仅是建议双方协商或向上级反应情况,并未对事件本身进行处理。当事人于2022年9月4日下午被抓获,但证据材料显示其被抓获前最后一次与主管单位经办人发生争执的时间是2021年9月27日,也就是说当事人是在事发一年后被采取了强制措施。
虽说对当事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期限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追诉时效的规定,但对于这类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罪名而言,当时并未造成严重后果,亦未追究责任,而是于事发一年后当事人无其他类似行为的情况下,乍然追究其刑事责任,无论如何评价,均是有其突兀的地方。更不必说其行为本身是否能够达到寻衅滋事罪的认定标准了。
二、司法实务中对寻衅滋事罪的认定
我国刑法第2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内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从刑法对寻衅滋事罪的量刑标准来看,该罪名是一个量刑较重的罪名,因此在入罪时也持相对谨慎的态度,要求行为具有情节恶劣或后果严重等情形的,才会构成寻衅滋事罪。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7月15日公布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第一条对寻衅滋事罪的起因进行了细化,认为行为人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这应该是对刑法做规定寻衅滋事罪构成要件的标准解释。该条第二款又规定行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纠纷,借故生非,实施刑法第贰佰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但矛盾是由被害人故意引发或者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主要责任的除外。第三款规定行为人因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纠纷,实施殴打、辱骂、恐吓他人或者损毁、占用他人财物等行为的,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但经有关部门批评直至或者处理处罚后继续实施前列行为,破坏社会秩序的除外。
上述两高司法解释中,明确将借故生非行为列入了寻衅滋事罪的处罚范畴,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19年4月9日印发的《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认为因本人及近亲属合法债务、婚恋、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而雇佣、指使他人采用“软暴力”手段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构成非法拘禁,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寻衅滋事,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但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仍继续实施的除外。但因为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本身就十分抽象,再辅以更加抽象的认定标准,实务中经常存在将这一类犯罪扩大认定的现象,这也是寻衅滋事罪经常受到法律界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实务界尤其是律师行业,对寻衅滋事罪这一罪名的存在本身就有很大异议,就更勿论为了实现合法诉求的轻微借故生非行为了。
三、对于借故生非的行为,应区分不同情况予以对待
(一)有正当诉求的轻微借故生非,不应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实务中发生的借故生非行为,多集中于久拖不决的邻里、婚恋、家庭、债权债务以及农村的土地问题。尤其是农村土地问题,涉及户籍变更以及土地档案资料的缺失,有些还存在征地、拆迁等大额经济收益,往往成为矛盾纠纷的高发领域。一般遇到这类问题在与行政主管部门沟通协调的过程中,因为非常难以处理,所以经常会遇到各种推诿的现象。对于很多基层百姓来说,这类情况通过诉讼解决难于登天,最便捷有效的方法就是去主管单位找负责人或经办人“讨个说法”。但是在现有的刑法规范条件下,这类“讨说法”的行为就会在犯罪的边缘行走,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寻衅滋事罪中的借故生非行为……,总是会有一款罪名能够对应当事人的行为。
但是从刑法设置寻衅滋事罪的立法目的,以及在涉黑涉恶类案件中仍坚持对轻微的“借故生非”行为不予处理的司法意见,对于日常生活中一些具有合理诉求且明显轻微的“借故生非”行为,更不应一刀切的认定为构成刑事犯罪,而是要本着教育引导为主,刑事处罚为辅的教育引导观念,告知当事人正确的解决路径。
(二)对于一般的借故生非行为,可以通过行政手段予以规制
当然,不排除实务中有部分当事人对自己的认知根深蒂固,根本无法接受他人意见,即便得到明确答复或建议之后,也仍然要我行我素,采用自认为正确的路径去救济所谓的“合法权益”。
对于这一类的行为,只要没有造成严重的人身或财产损失,亦没有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也是可以通过行政处罚的手段来进行教育规制的。比如对于一些轻微的影响了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正常工作秩序的行为,可以通过行政拘留等方式对其进行教育改造,让其意识到自身错误,并在将这类行为纳入刑法规制前,以因同类事由受到过行政处罚作为前置条件。
对于一些轻微的违法行为,行政手段往往更具有针对性:一方面不会对当事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长时间限制,有利于其自身思考改正;另一方面也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当事人采取一些过激行为的时候,一旦不服从处罚,立即依法对其进行拘留,防止出现类似本案中事发一年多又秋后算账的情况。
对于极少数受到上述各项处罚后拒不改正,仍执着于借故生非的当事人,再以寻衅滋事罪对其进行刑事处罚也未尝不可。
(三)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借故生非行为,亦可以根据情节认定为其他罪名
当然,实务中也不乏一些人在主张合法权益或者借故生非的过程中,用力过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进而触犯了刑法分则中一些涉及财产和人身权利以及社会管理秩序的罪名。针对这一类的情况,根据其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来定罪量刑,实务中并无太大争议。
总之,因为寻衅滋事罪名本身就是口袋罪的模糊属性,再加上很多所谓借故生非的人实际上是存在很多疑难问题久拖未决的。尽管其维权方式不值得提倡甚至应予以制裁,但考虑到他们本身就是弱势群体,维权的目的也并非获得不当收益,刑法在对这一类人群进行处罚的时候也应充分考虑其合理诉求,尽量以温和的方式来解决这类纠纷,保护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

皮兴兰律师
13637060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