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刷单炒信行为
行刑衔接问题研究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电子商务凭借着其方便快捷的优势正蓬勃发展,人们愈发频繁地在网络平台进行购物消费,这无疑是科技给人们带来的福祉。但是,网络购物平台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其所有的信息交流都不是面对面而是在电子屏幕前完成的,这就会产生信任的问题。在网购平台上,顾客对于店家的信任可以说是完全来源于店家的信誉,信誉在网络交易中便尤为重要,如此一来便给了不良商家可乘之机,利用网络刷单炒信来营造出一种信誉度高,产品质量好的假象。顾客由于难以分辨此种被刷出来信用真假,购买了商品,从而产生了消费权益纠纷,最终给网络购物带来信用危机,对电子商务领域造成严重冲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网络刷单炒信行为进行规制的必要性已不言而喻,相比于传统意义的刑法犯罪,刷单炒信行为具有显著的双重违法性,对于其违法性的认定包括了行政认定和刑事认定。因此,在行刑衔接视角下研究网络刷单炒信行为是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的。
一
相关概念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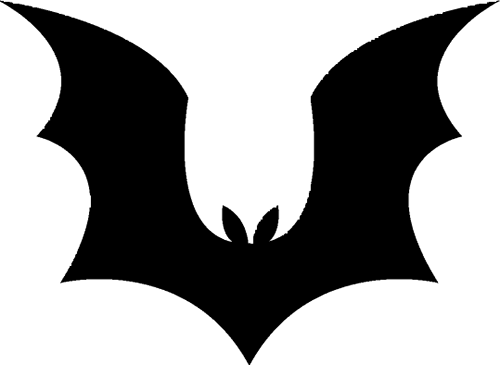
网络炒信行为作为一种口碑营销,它是“互联网+”的衍生物。顾客在网络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服务时,由于无法面对面真实地感受和接触,所以商家所售商品的销量、评价和商家的信用等级便成为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一些无良商家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通过网络刷单炒信行为进行虚构交易,从而达到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提升商品的销量、好评和信用等级的目的,这种恶性竞争无疑会扰乱网购平台的交易秩序。
为了遏制恶意刷单炒信行为,众多网购平台服务商和管理者已经对“网络刷单炒信行为”作出了相关规定,如《淘宝规则》将“炒信”定性为虚假交易,即“以不正当方式获取虚假的商品销量、店铺评分、信用积分或者商品评论等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同时,学界也对“炒信”行为展开了研究,其中一种关于网络刷单炒信的定义是:“炒信”是指在网络交易平台上,通过刷单、刷量等虚假交易方式炒作商家信用的行为。
在法律文件中,多将常见的虚假交易、虚构好评或者删除差评等网络刷单炒信行为规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处罚方式一般为行政处罚。可见,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法律文件中,对于网络刷单炒信行为的概念并未形成统一的界定。本文根据对网络刷单炒信行为的分析得出其具有易发性、智能性、复杂性、高危型、行政违法性以及刑事违法性的特征,因此网络刷单炒信行为可以定义为“任何个人、团体或者组织出于非法目的,为了虚假提升信用水平,故意使用虚假交易、删除不利评价等方式对信用评价体系和网络交易秩序造成严重威胁或损害的违法犯罪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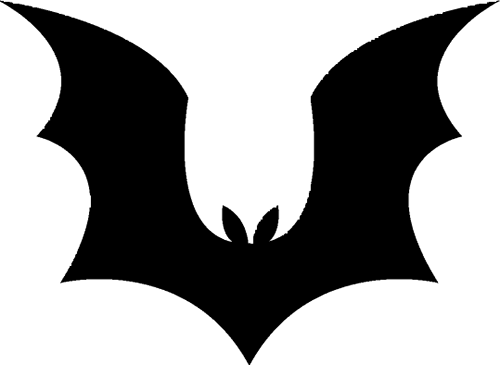
行刑衔接,又称“两法衔接”,是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相衔接的简称。“行刑衔接”的提出源于行政执法机关在规制经济犯罪案件过程中出现有案不移、以罚代刑等现象,旨在启动并实现刑事追诉,强化刑事司法向行政执法领域的渗透。行政法和刑法是公法领域两大主要的法律手段,其对于网络刷单炒信行为的规制作用举足轻重,因此需要梳理“行刑衔接”的理论脉络,找出“行刑衔接”的制度症结,在立法层面构建相互配合又分工明确的网络刷单炒信行为“行刑衔接”机制。
二
问题检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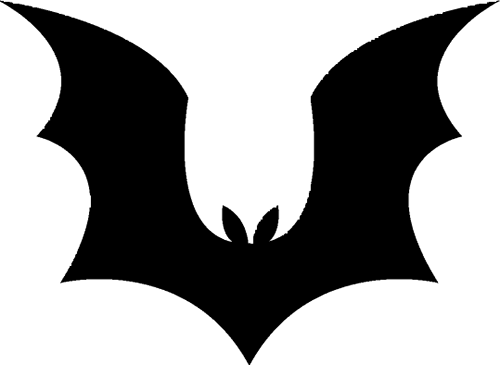
作为在网络刷单炒信领域的“行刑衔接”,其具有和食品安全、药品监管领域“行刑衔接”相类似的共性,但是也有不同于它们的独特属性,不可一概而论。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行刑衔接”的研究多集中于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领域,对于立法层面的研究较少,“行刑衔接”机制的构建不可能脱离立法只关注执法和司法,因为立法是执法和司法衔接的前提,是“行刑衔接”的研究基础。在立法衔接上要通过行政立法和刑事立法准确划分网络刷单炒信行为的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的边界和范畴,只有在静态的立法衔接上做到了行政立法和刑事立法的协调,才能在动态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上为双向移送机制赋能。
在立法层面的衔接问题主要是关于网络刷单炒信行为的刑事法律和前置法中“涉刑”规范的协调统一问题。对于网络刷单炒信行为的规制不是能够仅仅依靠刑法,这同时也是刑法谦抑性的内在要求,想达到对网络刷单炒信行为良好的规制效果,就必须做到刑事法律规范和前置法的统一协调。2019年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条文中涉及的对网络刷单炒信行为的规制理念体现了和《刑法》的相互配合,但是二者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不协调、断层以及模糊之处,主要体现在刑事法律和前置法立法规定脱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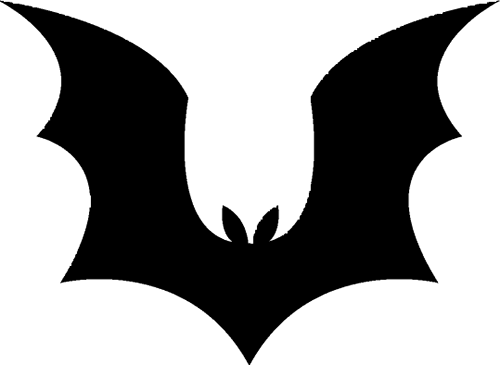
(一)附属刑事罚则被束之高阁
基于维护刑法典体系性和稳定性的考虑,我国附属刑事罚则多数是规定在行政法律规范等非刑事法律中,其本意在于寻求简约刑法和惩治犯罪的平衡,但由于规定内容过于笼统、模糊,因而难以被应用到司法实践中。比如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组织虚假交易、虚假宣传用户评价等网络炒信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没有明确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和条件,而且刑法典中缺少具体的罪名与之相对应,导致前置法中的规定功能被虚置,沦为“宣示性条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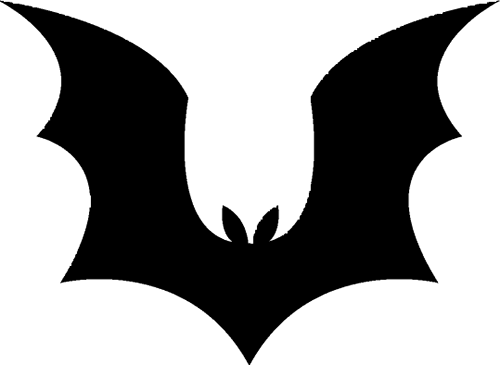
(二)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衔接不紧密
对于网络刷单炒信行为的行政处罚主要有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营业执照等方式,若构成犯罪的,则适用罚金刑、拘役、有期徒刑等刑罚处罚方式。因为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是呈递进状态且相互联系的,那么对于其处罚方式也应当具有相应的层级,但是从目前的立法来看,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衔接不够紧密。主要表现在罚款和罚金刑金额差异较大,根据责罚相当原则,针对同一社会失范行为,其犯罪行为的罚金下限应当高于行政违法行为的罚款上限。但是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网络刷单炒信行为的规定,其最高可罚至200万元,但是刑法对于该行为的罚金刑并没有明确的数额规定。如此一来,司法人员便失去了易操作、易适用的判断标准,无所适从就会弃之不用。
三
完善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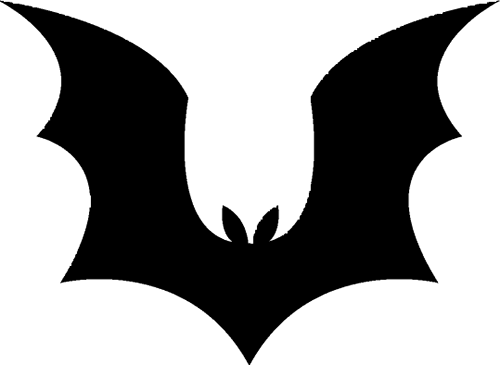
(一)明确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
要在司法实践中准确对网络刷单炒信行为进行规制,则需依赖于在立法层面对该行为的精准界分,明确行为“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可以通过学术界提出的“质量说”将定性和定量结合起来对该行为加以规制。将危害程度作为界分网络刷单炒信行为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主要依据,将行为类型的界分作为辅助和补充依据。
首先在行为的定量标准上,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主要的区分标准是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不同,但由于我国刑事法律条文中对于危害性的程度多用“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严重后果”、“特别严重后果”等用语,此类用语过于模糊笼统,给司法实践中对网络刷单炒信的规制造成了困难,建议在行政立法和刑事立法的完善中,对于涉及到以危害程度作为界分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重要依据的行为,应当对造成的后果的大小、数额多少、情节严重程度等进行具体、明确的规定,使行政法规范和刑法规范实现协调统一。唯有如此,才有助于行政机关准确判定网络炒信行为是否涉嫌构成犯罪,进而将其移送给刑事司法机关,实现两法衔接。
其次是在行为的定性上,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不是一一对应的,不能认为当网络刷单炒信行为超过一定的限度就转化为刑事违法行为,还需要关注该行为是否具有犯罪化的特征以及在刑法上是否具有可谴责性,不能只从危害程度这一“量”上孤立判断。比如,针对网店经营者通过亲戚、朋友等帮忙代刷的方式来提升店铺的销量和信用等级的单刷型炒信行为,其实质上是网络交易竞争中卖家理性选择的结果。即使单刷型的网络炒信行为在行为人数、数额、损害后果、实施次数、情节等量化要素表现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立法上也只能将其规定为行政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而不宜犯罪化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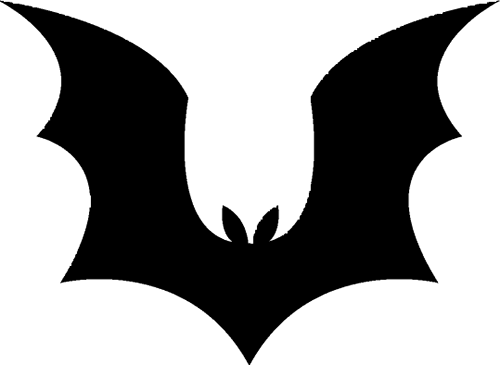
(二)完善刑罚配置
贝卡利亚说过:“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这种大于好处的恶果中应该包含的,一是刑罚的坚定性,二是犯罪既得利益的丧失。”
对于网络刷单炒信这种趋利性违法行为,应当完善我国法律对该行为的罚金刑规定。正如上文所述,我国行政法规中的罚款和刑法中的罚金衔接不够紧密,刑法的附加刑对于网络刷单炒信犯罪主要采取的无限额罚金制或者比例罚金制的立法方式,这种数额规定模式过于依赖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罚金若没有明确的裁量标准,司法人员或因裁量权过大而造成处罚结果畸轻畸重,有失公允,或因无明确标准而无所适从,弃之不用。为了解决罚款和罚金在金额大小、轻重衔接上的不平衡,应当完善相关刑事法律规定:一方面,刑法上应取消无限额罚金制或比例罚金制,对网络刷单炒信行为适用相对确定的法定附加刑,以此限制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刑事法律在条文规定上应当明确对于侵犯同一客体的违法犯罪行为,罚金刑的下限一般应当高于罚款额的上限。这既是“行刑衔接”在制裁轻重方面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内在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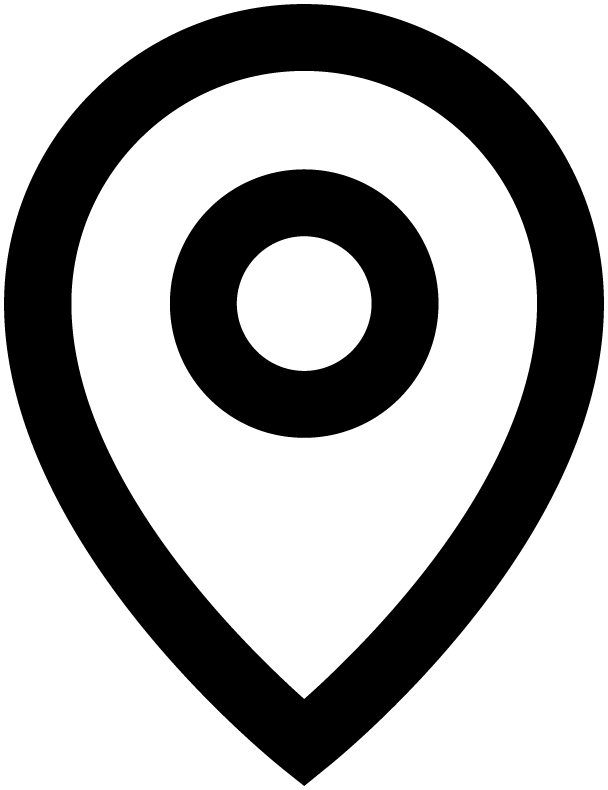
高云龙
合肥工业大学在读硕士
润天律所见习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