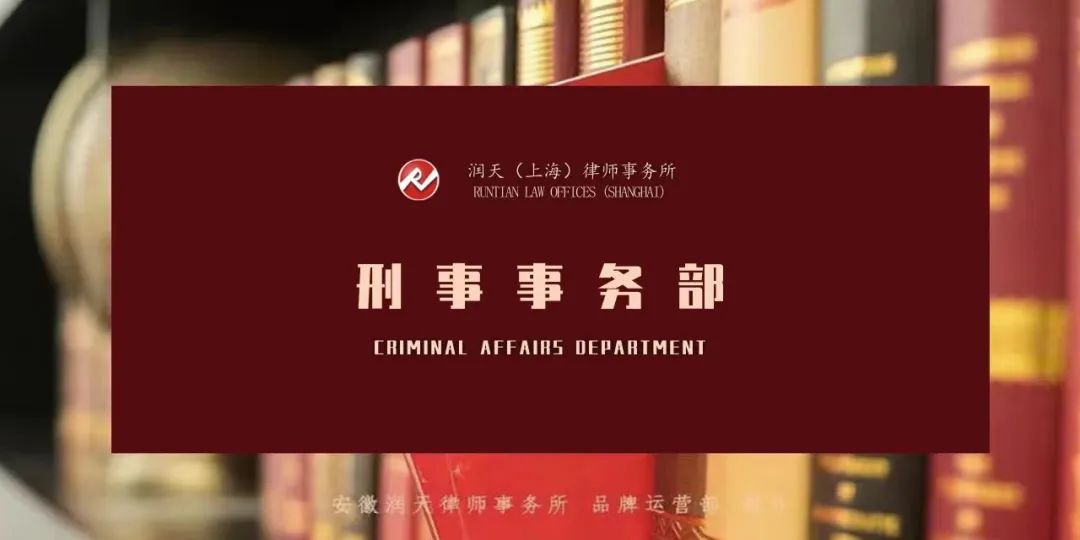
“软暴力”型催收非法债务罪中“恐吓”认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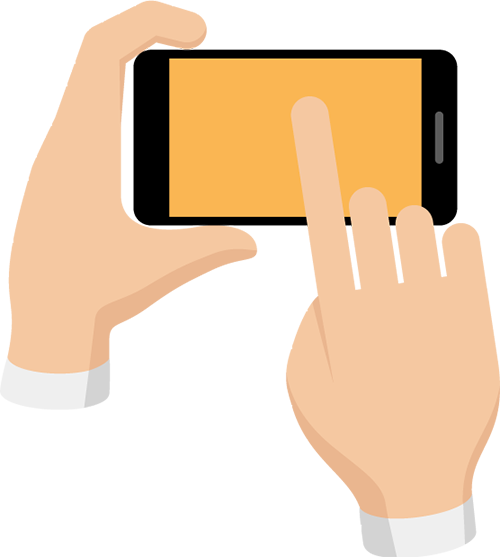
一、研究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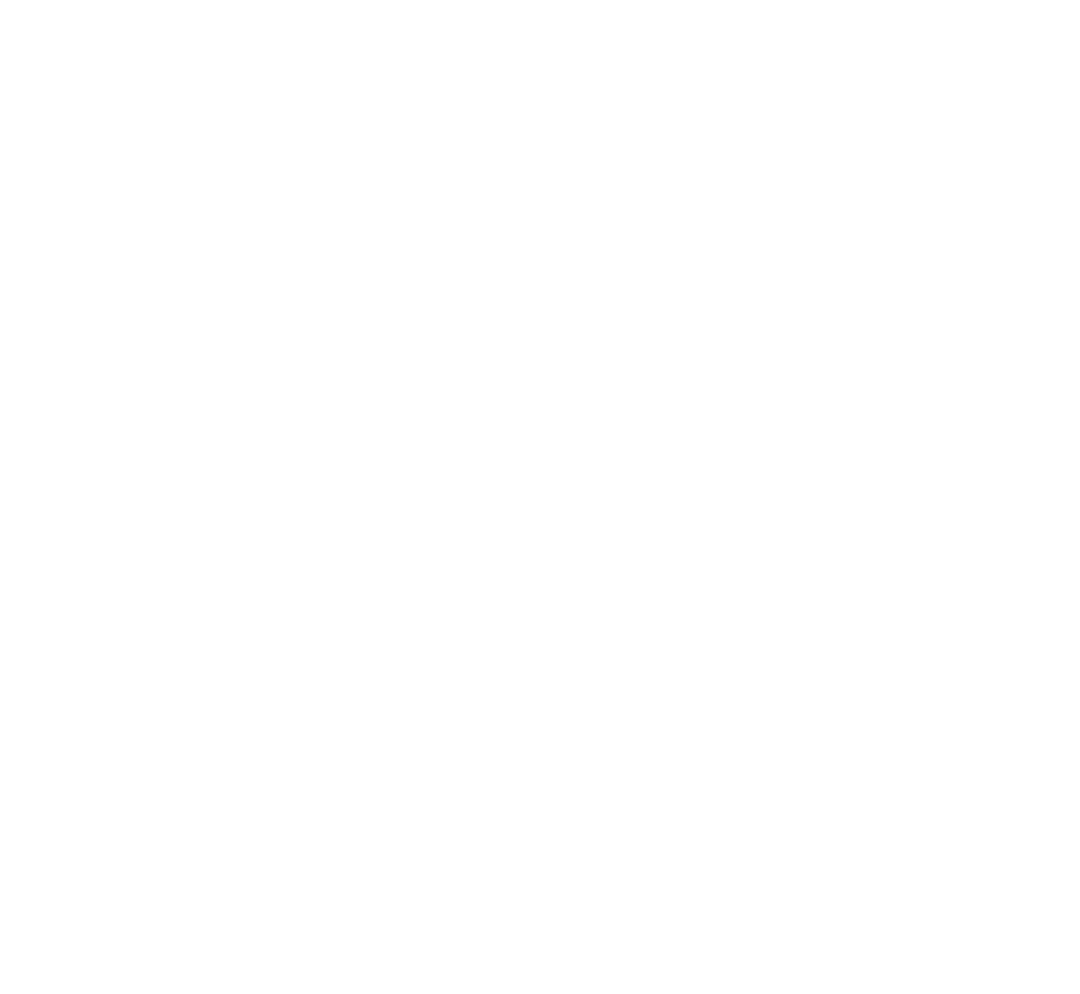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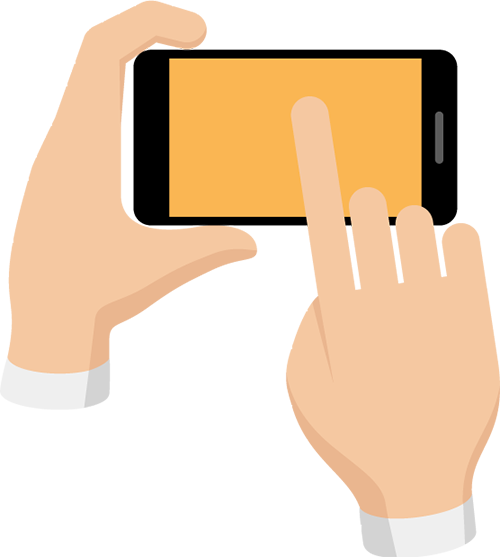
二、“软暴力”犯罪特征明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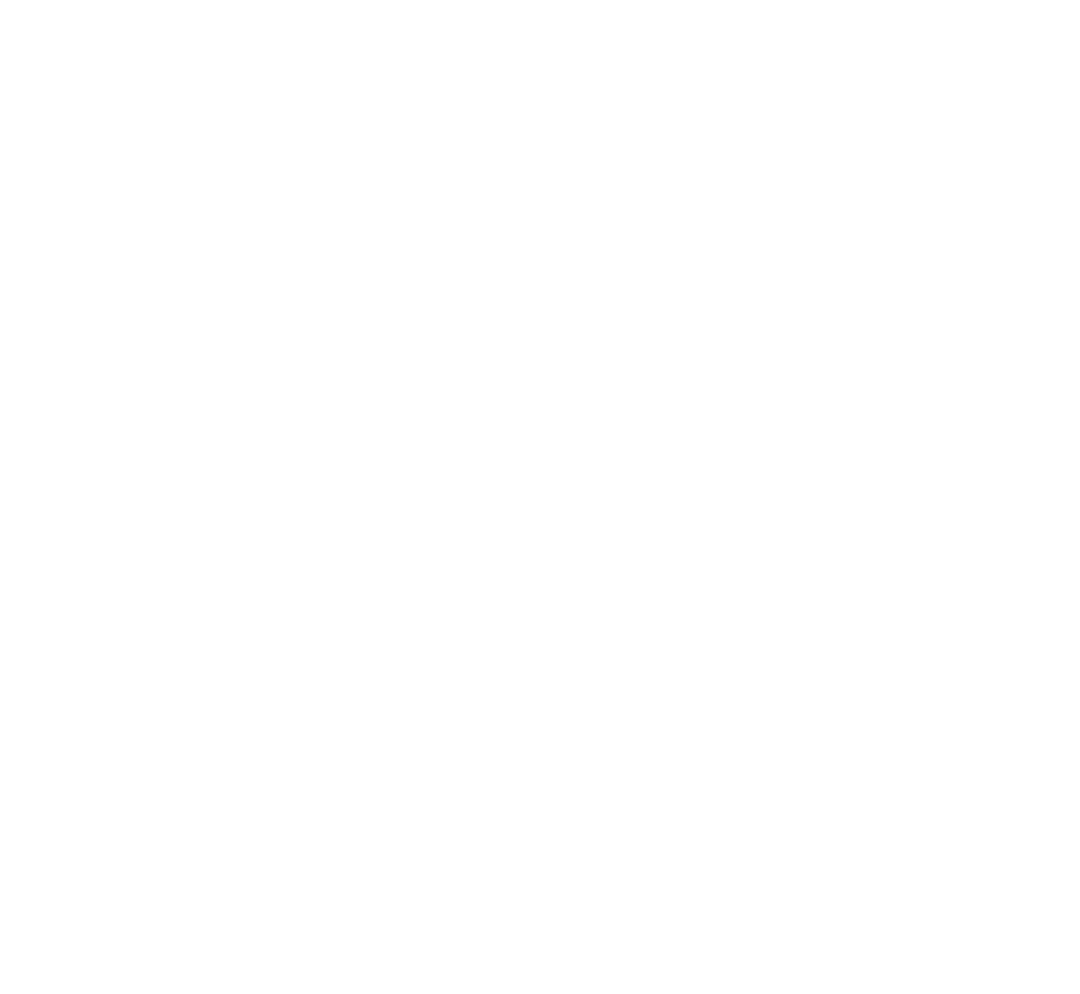

(一)隐蔽性
软暴力犯罪具有隐蔽性,往往难以区分。通常并不是使用暴力,而是利用自身影响力或者暗示等手段使他人感到恐惧,进而达到相应目的。虽然 2019 年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于“软暴力”进行明晰,但是由于定性难度较大,在司法实务中仍然有许多软暴力犯罪逃避处罚,部分司法人员为了避免争议,往往采取行政处罚这种无关痛痒的处罚,使得犯罪分子的犯罪成本大大降低。另外,犯罪分子通常将获得的不法债务进行及时的“洗白”,通过开设公司,合法经营等,极大地加大了对软暴力犯罪的侦破。因此,软暴力犯罪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二)证据获取难度大
由于犯罪集团的影响力较大,往往采取间接的、非接触手段即可实现非法目的。因此,对其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也难以充分确定,证据固定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比如,以套路贷为例,受害者陷入套路贷陷阱,往往其并不自知,对于行为人的犯罪事实并不能及时洞悉,从而无法收集和固定相关证据材料;另一部分人,可能慑于犯罪集团的威势,即使意识到犯罪分子的不法行为,也不会主动提起相关诉讼或者固定证据,部分证人出于安全考量也不会出庭作证。并且由于被害人通常情况下处于弱势地位,靠其自身力量很难获得证据。综合来看,软暴力犯罪获取证据的难度非常之大。
(三)量化困难
普通的刑事犯罪或者以暴力手段催收非法债务所造成的后果往往直接清晰,相关法律将根据犯罪后果予以定罪量刑。例如,对他人实施故意伤害罪,造成相应的轻伤、重伤等都有明确的鉴定标准,法检仅需根据相应的鉴定意见进行量刑即可,并由行为人承担赔偿乃至刑罚责任。但是由于软暴力犯罪的特殊性,其对被害人往往并未造成直接的、可衡量的损害,而是对被害人造成心理负担、陷入心理强制、对其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等抽象情况。例如,在一起案件中,行为人坚持与受害者同住同睡,严重干扰其生活秩序,这种情况很难对受害者的损害进行具体的量化以及赔偿标准。在此背景下,往往极度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因此,现实生活中在刑罚量化方面存在诸多争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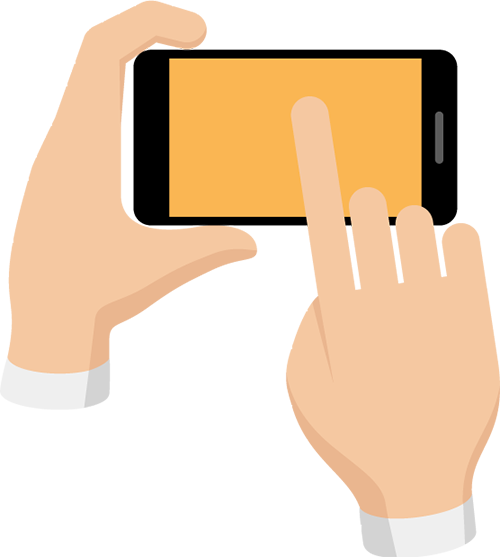
三、“软暴力”催收行为中“恐吓”认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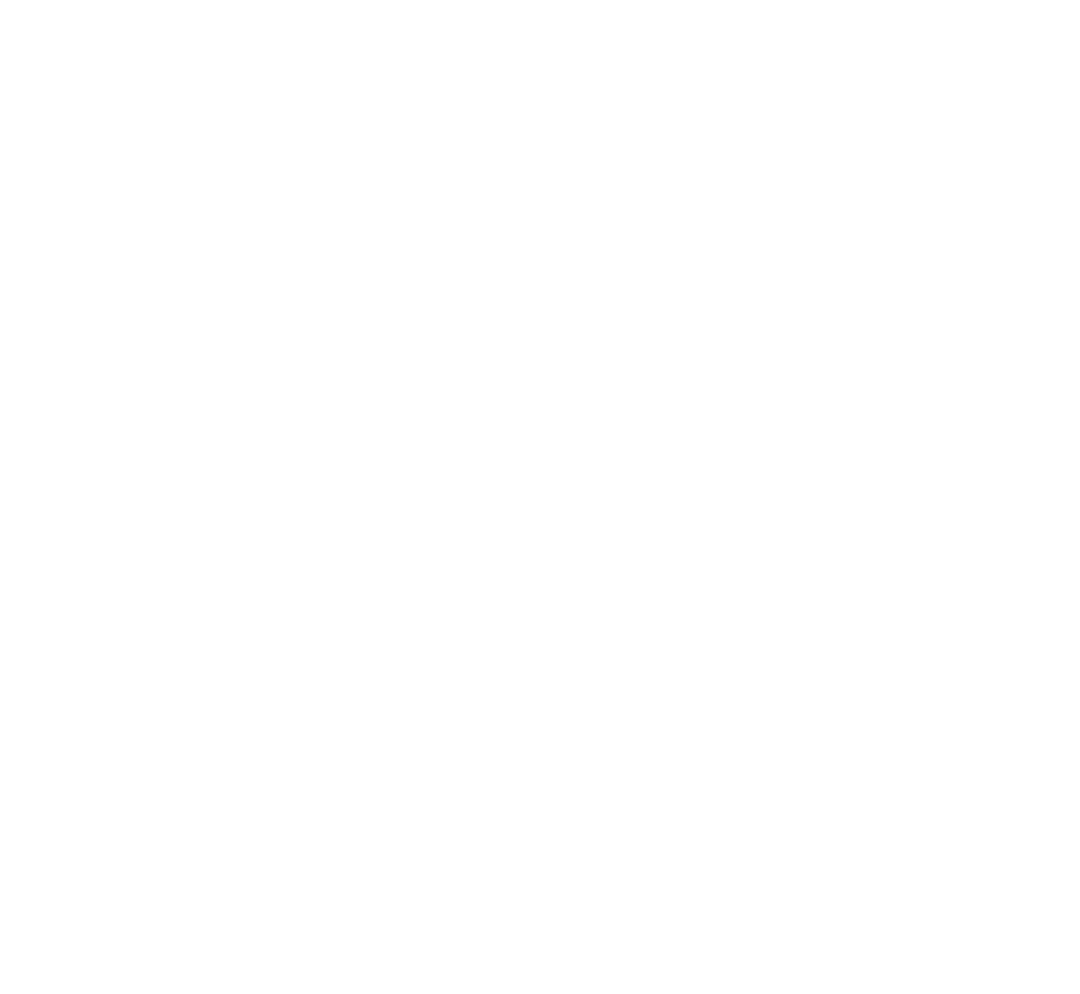

(一)“恐吓”概念界定
“恐吓”,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具有较大的歧义,但其本质仍是“以恶害相通告”,所以在司法实务中认定是否构成“恐吓”,需要牢牢抓住其本质。首先,在进行“恐吓”的相关分析前,我们需要将其和胁迫、暴力等进行区分。不难看出,由于现行立法单独划分出“恐吓”,则证明此三者为并列关系。因此,恐吓不应当包含任何暴力手段。从概念入手:首先,对受害者实施“完全暴力”(即直接身体接触),则不属于恐吓行为;其次,以预告未来的身体侵害,并使得受害者产生安全威胁的,应当归属于胁迫,虽未预告未来的行为,但行为人实施足以使得被害者产生心理压迫,具有较严重的安全威胁的,也应当归于胁迫,如手持刀具与被害人进行沟通等。综上,但凡对被害人人身安全有着紧迫侵害或者人身安全有着现实危险的,均不归属于恐吓。
(二)“恐吓”内容的分析
恐吓内容基本涉及对受害者人身权、自由权、财产权、名誉权等的侵害。但并非所有此类侵害都能构成恐吓。首先,仅仅是对抽象观念性的权利侵害并不能构成恐吓,比如以侵害拥抱权为由进行恐吓,显然无法得到认可;其次,即使内容不明确,但足以使得受害方联想到自身权益的侵害,也可以构成恐吓,比如,行为人威胁:如果三天不还钱,我知道你家住址,后果自负。但是可能有学者提出质疑,此刻足以对被害人产生紧迫的安全威胁,应当构成胁迫,但私以为,此刻内容不明确,如果将其笼统的归结为胁迫,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也不利于被告权利的保护。最后,是对受害者财物的侵害,主要探究其行为是否足以影响被害人人身安全,比如拦路砸车,对被害人人身安全产生威胁,则分情况构成暴力或者威胁,如果被害人不在车内,则无法或者较少影响到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则构成恐吓。
(三)恐吓行为的分类
对恐吓行为的分类有多种方式,有以权益侵害的类型进行分类,有以恐吓方式进行分类。本文采取后者,相比于前者,第二种分类更加清晰简单,也能够被大众所普遍接受。
1.语言恐吓与行为恐吓
语言恐吓,顾名思义,就是通过以言语方式传递恐吓内容,此类恐吓简单清晰。这也是催收非法债务的前期阶段,是犯罪集团等非法催债公司的普遍使用方式,但由于语言恐吓效果不佳,且易被固定为证据。因此,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紧接而来的是行为恐吓,行为恐吓又分两种,一种是所谓肢体语言动作、暗示行为等,此类较为隐性,是现阶段较为常用手段,而另一种则是聚众哄闹,关于此类是否构成恐吓尚有争议,本人认为此类行为有构成恐吓的可能,因为一方面其具备使得受害者产生恐惧的行为,另一方面,其也存在进一步侵害权益的潜在意思,因此,构成行为恐吓,但需要注意区分其与跟踪、骚扰的区别。另外,除却语言恐吓和动作恐吓,不作为的恐吓也可能存在,如行为人将受害人推入河流,也不救助进行恐吓,当然,这也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这另当别论。
2.网络恐吓与面面恐吓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短信、微信、视频等方式进行恐吓的逐渐增多。例如,以裸照为由进行恐吓。网络恐吓相比面面恐吓存在两类问题,第一,网络恐吓和面面恐吓相比,前者所造成的影响可能仅仅局限于行为人和受害者两方,而面面恐吓所造成的范围影响则较大;第二个问题则是相比面面恐吓,网络恐吓对于受害者所造成的心理压力较小,由于这两类问题,往往对于网络恐吓的判定则更加困难,因此,诸多网络恐吓逍遥法外,而随着现今净网行动的展开,我们需要对网络恐吓有着相应的明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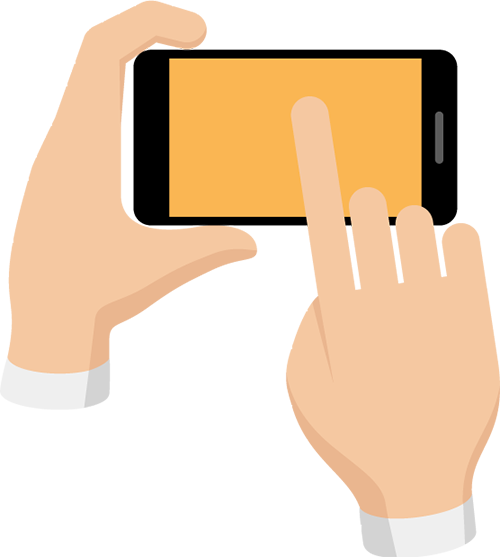
四、恐吓需要以妨害社会秩序为必要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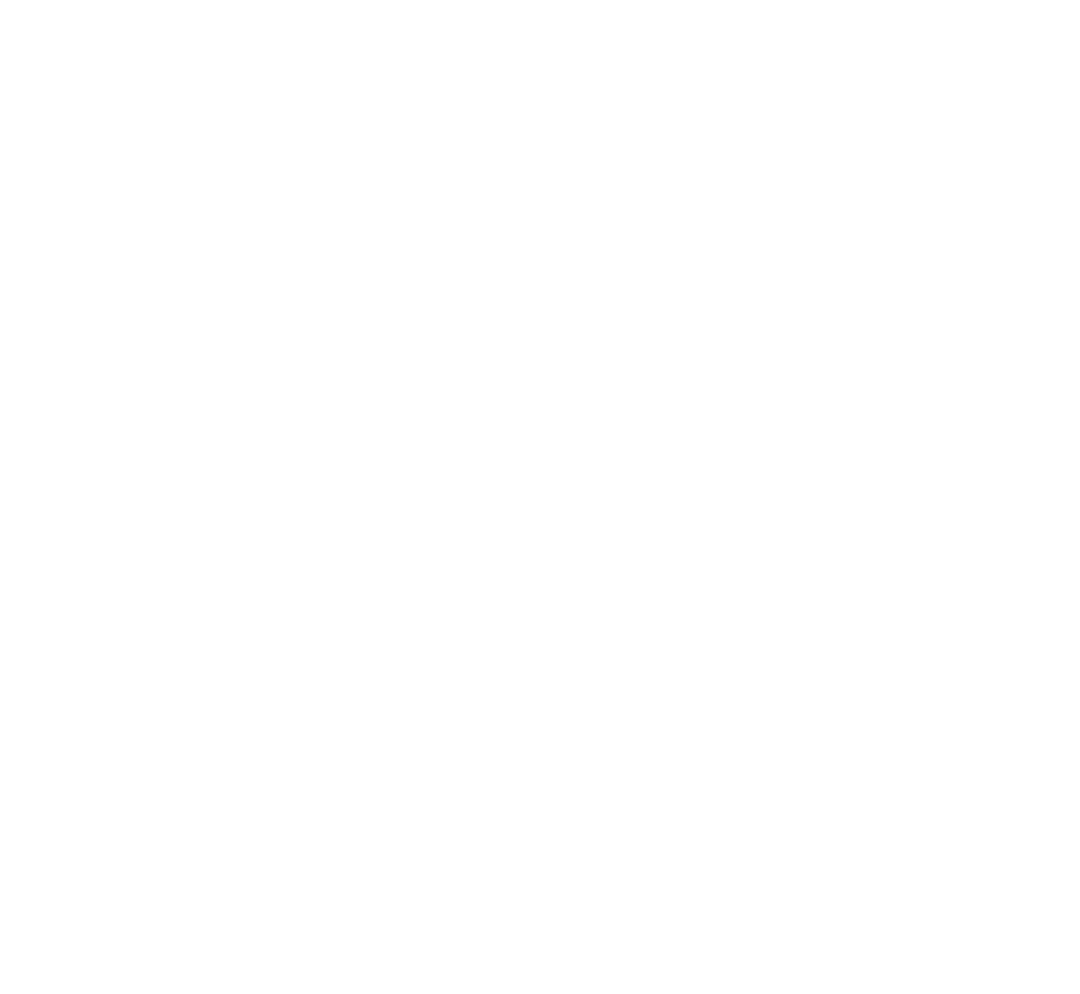
这是目前学界争论较多的问题,就本人而言,我认为需要以妨害社会秩序为必要条件,现实恐吓虽然可能存在较为隐蔽的一对一情况,但是由于恐吓需要多个频繁行为,因此,尽管可能没有任何暴力行为,但是这种隐形压迫会使得被害人的心理恐惧进行放大蔓延,进而延展至身边不特定多数人。而网络恐吓也对应侵害相应的网络公共秩序,为了方便理解,将公共秩序等同为我们现实生活的社会管理秩序。在网络中传播带有明显的暴力因子,如残害动物的血腥视频,此刻已经具备妨害社会秩序,当然,需要根据传播量、点击量等进一步界定,如果并非暴力性内容,仅仅是对他人名誉的侵害,此刻,受害者的名誉权益时刻处于被侵害的状态,而这种恐惧感也会随之蔓延至其他网络成员。因此,恐吓型的催收非法债务罪也需要以妨害社会秩序为必要条件。
总之,软暴力型催收非法债务罪有着隐蔽、难以量化、证据获取难度大等特征,但是由于现阶段软暴力犯罪较为突出,我们需要进行清晰界定,而在软暴力催收非法债务罪中,恐吓则尤为突出,对于是否构成恐吓,我们需要对其概念和分类进行明确,并且需要统一观点:需要以妨害社会秩序为必要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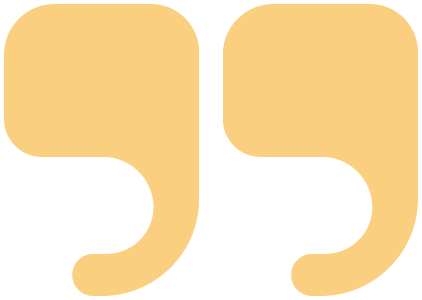

方雨杰
合肥工业大学在读硕士
润天律所见习生
润天律所
合肥工业大学研究生见习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