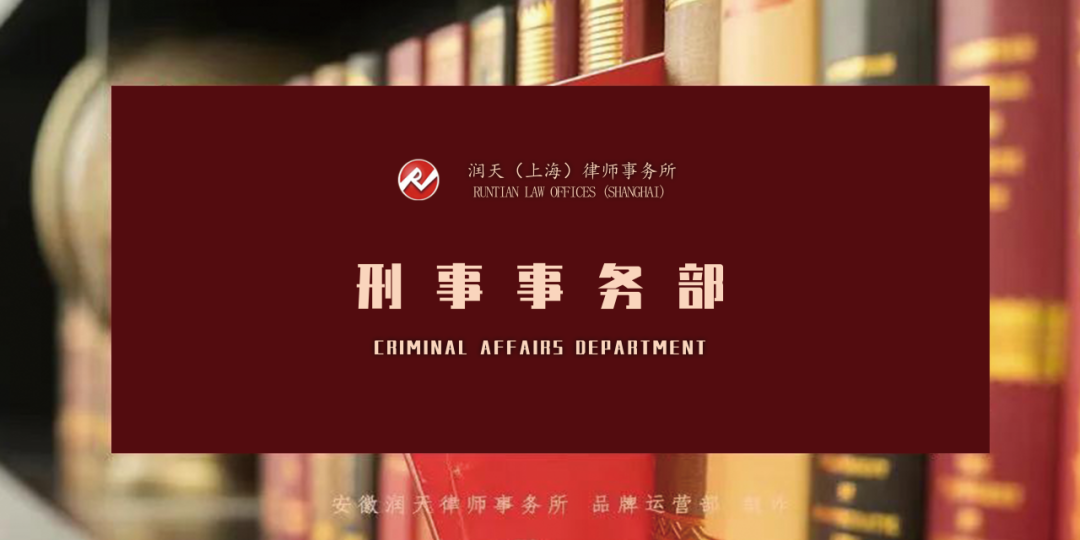
刑附民案件
“两金”赔偿的合理性分析
刑附民案件的“两金”赔偿,指的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被害人或被害人近亲属主张的“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尽管以笔者的视角认为精神损害赔偿亦应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之内,但因现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75条中对此已经明确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并且理论界较为通行的说法是认为被告人已经受到更为严厉的刑事处罚,被害人及家属的精神损失已经得到适当弥补,因此认为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有一定的合理性,本文在此暂不做过多分析。
一、分析背景
笔者近年作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被害人代理人或被害人近亲属代理人,参与了多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办理。期间经过对相关法律法规及案例的检索,发现自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起草小组成员在《人民司法》第7期上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后,实务中再难以见到支持“两金”赔偿的案例;反倒是此前明确不被支持的“精神损害赔偿”,因2021年3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的表述有所松动而获得了极少数的支持。
笔者相信最高院收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赔偿项目的范围,自然有其理论和实务依据,但通过办理该类案件过程中与被害人或被害人近亲属的多次接触,更能够体会到其合理诉求无法获得法律支持的挫败感,以及自身受到损害后的赔偿要求无法获得法律支持的无力感。尤其是一些重伤害类案件,被害人的人身往往遭受了巨大的伤害,但仅能从被告人处获得有限的赔偿,根本不足以弥补其遭受的损失。因此笔者认为无论是作为法律法规的制定者还是施行者,都应当一切从群众的实际利益出发,经过深入调研而得出最有利于人民群众的结论。
二、我国刑附民“两金”赔偿规定的历史沿革及司法现状
(一)我国刑附民“两金”赔偿规定的历史沿革
我国1979年7月7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提出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其第53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此后的历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基本沿用了这一规定。但是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范围的限定,实际经历了不同的理解。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6年公布实施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的通知及1998年公布实施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均规定“人民法院审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因此在当时的司法环境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基本是参照相关民事法律的规定进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公布实施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5条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范围做出了较为明确的限定,该条规定中并未将“两金”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但实务中一般仍解读为两金赔偿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并且裁判文书网中也能检索到很多刑附民案件中支持上述“两金”赔偿要求的判决。
(二)我国刑附民“两金”赔偿的司法现状
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仅以四条内容对附带民事诉讼进行了概括性规定,实务中多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相关条文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进行规制,但该司法解释中并未明确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列入赔偿项目。在此前提下,仍有部分地区高院依据相关民事法律的规定,将“两金”纳入赔偿范围,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四川省高院于2020年11月印发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意见》中,明确将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此前陕西高院、天津高院等也陆续发布过类似的意见。
2021年现行《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发布后,尽管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赔偿项目问题并未作出修改,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司法解释起草小组成员于《人民司法》2021年第7期中,以对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的形式,认为基于被告人普遍无力赔偿以及“空判”所引发的系列问题等考虑,不应将“两金”纳入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赔偿范围。虽然该理解与适用并不具备强制性的效力,但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倾向性意见,已经成为各级法院的共识。
现在代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过程中,法官往往也会在庭前或庭审中释明不会支持“两金”和精神损害赔偿,判决书中自然也不会予以支持。笔者代理的一起被害人死亡的故意杀人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一审判决中,仅支持了约四万元的丧葬费,被害人近亲属无论经济上还是精神上的损失,都无法据此弥补。
三、应将“两金”纳入刑附民案件赔偿范围的理由
(一)法律应更好的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作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尤其是一些受到严重伤害导致重伤残的被害人,其本人和家属此后的生活往往就依赖于被告人的赔偿,而在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支持残疾赔偿金的前提下,被害人不仅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甚至连正常的生存都会面临严峻的挑战。
上述理解与适用中,认为不能将“两金”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赔偿范围的理由,主要是基于平衡被害人对该赔偿的高期望值与被告人极低的赔偿能力考虑的。但民事诉讼实务中类似矛盾极多,也并未以避免社会矛盾激化为由阻碍权利人相应权利的行使;作为社会矛盾处理最后一道防线的刑事法律法规更不应轻易放宽对被告人的经济制裁,而应参照相关民事法律的规定判决被告人对被害人的相关损失予以赔偿。
司法实务中,被害人更多的可能会因为自身的合理诉求未获得法律支持或者被告人具备赔偿能力拒不赔偿而寻求其他救济途径,但因为被告人已经被执行死刑或者被收监执行,无个人财产可供赔偿而迁怒于司法机关的可能性还是较小的。并且会因为司法机关的判决无法执行而迁怒于司法机关的当事人,可能无论法院如何判决都无法达到他们的满意,限制他们受到赔偿的范围仍然可能会引发他们的激烈反应,因此无法达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
实务中也无需担心被害人因为对赔偿数额的期望值过高而影响案件调解,毕竟对于被害人来说,接受调解就意味着能够更快、更顺利的得到赔偿;部分被告人家属可能出于让被告人获得从宽处罚的目的,也愿意代为支付相关赔偿费用。
(二)将“两金”纳入刑附民的赔偿范围能对被告人起到更好的震慑效果
目前有部分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因为明知不达成调解协议被害人能够获得的赔偿数额极为有限;而自身即便因为主动赔偿获得从宽处罚,短期内也无法赚取与赔偿数额相当的金钱,也就是“宁愿多坐牢也不愿多赔偿”,从而导致被害人的损失无法获得有效赔偿。
另对于一些有赔偿能力的被告人,若明知不主动赔偿最终也会因法院的判决而被强制执行,其主动赔偿的意愿可能也会更加明显。
(三)简单粗暴的否定“两金”赔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
民事案件中人身损害的“两金”赔偿同样可能会面临“空判”的结果,但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并未因此取消对“两金”和精神损害赔偿的支持,也鲜少见到当事人因为法院的判决未获全额执行而申诉或上访的情形。因此,导致被害人申诉或信访的原因从来都是自身诉求未能获得支持,而不是被告人不具备赔偿能力。
另外无论从我国民事还是刑事立法的目的来说,均是为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而将“两金”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从明显受到更严重侵害的刑事案件被害人的赔偿中剔除,明显是不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的。
从司法实践来说,多数刑事案件的被告人都是主动选择了犯罪行为,而被害人则悲催的成为了被动接受的对象,其人身受到损害往往是其自身不可控的。那么在其人身受到明显不可控因素侵害的情况下,合法权益还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对于被害人来说更是明显不能承受之重。
综上,无论是从惩治犯罪,还是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或者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来说,将“两金”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都具有极大的合理性。

皮兴兰律师
13637060630



